饮食记忆:扒榆树皮的日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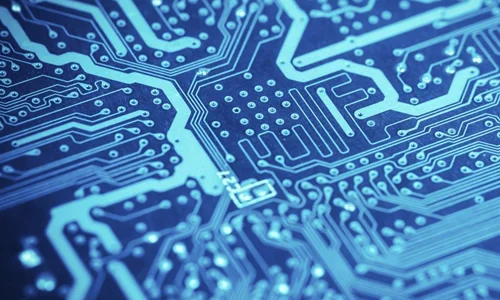
榆树皮
前几日到一个小山村里走亲戚,偶然间看到一户人家正在砍伐一株粗大的榆树。随着电锯“刺刺啦啦”一阵响过之后,突然,“咔嚓”一声,那棵足足有一人粗的榆树便轰然倒下。手握电锯的汉子,又动作非常麻利地将枝梢一一抹掉,十几个青壮劳力喊着号子,把直挺挺的树身抬上卡车,就拉走了。树根没人刨,树枝无人要,实在有些可惜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小时候扒榆树皮、吃榆皮面的情景。
儿时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,平日里别说吃顿白面(小麦面),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是非常稀罕;玉米面只能是隔三差五地改善一下,日常的主食便是既黑又无营养的地瓜面。地瓜面子非常松散,没有黏性,要是擀面条、拍呱哒,或者包水饺,根本成不了个儿。这里刚下锅,那里就散了架,真的是烂成了一锅粥。为把粗粮做出细粮的味道和模样,聪慧善良的父老乡亲便就地取材,用榆树皮面作黏合剂,这样做出的面食既筋道爽口、有模有样,又光滑顺溜、常吃不厌。
那时候,榆树是乡间主要的用材树木,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、院内院外,都栽植着三五株。盖房或者做农具的时候,就杀它几棵(我们这里把伐树称为“杀树”)。粗大而挺拔的,当做梁头;一掐粗的,作为屋团;弯曲些的,就用大锯由头到根纵向劈开,一分为二,两半木料弯度一致,左右对称,作为马车或地排车的两根车干再合适不过。但不论做什么用,树砍倒后,都须尽快剥掉树皮。去皮后的树身,干得快,干得透,还防虫蛀,便于使用。
那些年月,若是谁家杀了棵大榆树,女主人就到当街喊上几嗓子:“扒榆皮了!扒榆皮了!”闻声而动的街坊邻居,便纷纷提着锤子、镰头刀子,端着柳条筐或者簸箕,后面还跟着个半大孩子,以便打下手。腿脚快些的,便抢得先机,拣皮质最好的树根部分扒皮,而那些紧催慢不打的人家,只有扒树身的份。虽然同是一棵树上的皮,但树身与树根却有着不小的差别。根部的皮不仅厚实,出面率高,黏性大,而且还有淡淡的甜味,颜色也很纯正,呈紫红色;而树身上的皮就薄且硬,非常糙,含渣多,色泽也差了许多,白煞煞的。所以杀树的时候,树坑都挖得特别大,就是为了多取些根部的皮。
大人们手举锤子,“亢亢”地在树皮上不停地猛砸,让其与木质部分脱离,再用镰刀划出一条细缝,伸手轻轻一扯,树皮便像金蝉脱壳一般剥落下来。孩子们便两手并用地向筐里捡拾。不大会儿工夫,整棵树就被扒得干干净净,光滑洁白的树身在阳光照射下很是耀眼。
榆皮扒回家,老人们就趁湿用刀具轻轻地刮去表面那层皴裂的皮,然后等它晒干,到石碾上反复碾压,细密的箩筛出粉色的面,盛到盆盆罐罐里。和地瓜面的时候,就顺手捏上一小抓。记忆中,母亲这样做出的窝头或者卷子是家常便饭,一年四季不曾间断。
扒榆树皮的岁月,虽然已经过去近三十年,如今再次想起,依然感到亲切和温馨,但其中分明又夹杂着几分伤感与落寞。

